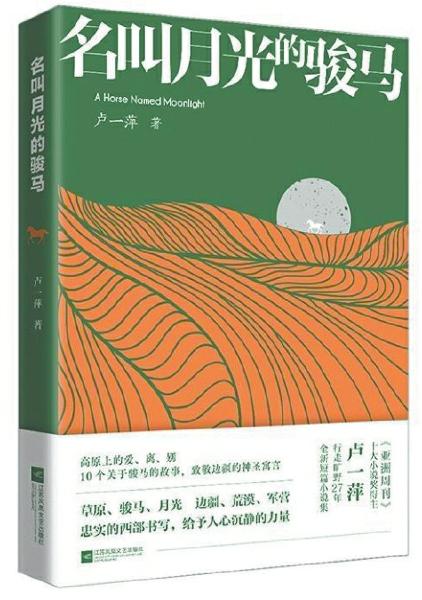-
马啸文苑 从诗卷风骨到精神长鸣
-
品
□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姗姗
从《诗经》里“萧萧马鸣,悠悠旆旌”的沙场剪影,到历代作家笔下承载灵性与思辨的生灵,马,这一兼具力量与温情的动物,始终是中国文学中永不褪色的文化符号。它是速度与自由的化身,是忠诚与勇气的象征,更是文人墨客寄托情志、观照世事的精神载体。
2026马年来临之际,记者循着文字足迹,穿越千年时光,聆听圣贤先哲与当代写作者们的马语心声,探寻这一意象背后跨越时空的深层意蕴。
诗文中的精神图腾
《诗经》中的“驷驖孔阜,六辔在手”,勾勒出君王驾车狩猎的雄姿,4匹黑骏马体态雄健,缰绳在手中收放自如,尽显驾驭者的豪迈与从容。岑参的《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》中“马毛带雪汗气蒸,五花连钱旋作冰”,以极致的笔触刻画了边塞战马的坚韧,雪水与汗水交融凝结,却依旧承载着将士们奔赴沙场的决心。
这些早期文字,既展现了马在古代社会生产、军事中的重要作用,也赋予了其勇武、忠诚的初始品格。
庄子在《马蹄》中对马的本性进行了深刻剖析:“马,蹄可以践霜雪,毛可以御风寒,龁草饮水,翘足而陆,此马之真性也。”他批判人为束缚对马天性的摧残,主张顺应自然,让马回归本真。这种对自由的追求,成为后世文人书写马的重要精神内核。
韩愈《杂说·马说》中“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”的感叹,既是对人才被埋没的惋惜,也让马成为人才的象征,伯乐相马的典故就此流传千古。
谈及汉唐时期的名马与诗作,文化学者康震有着生动解读:“大家常听说的汗血宝马,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生理特征——它容易出汗,皮肤又薄,皮下毛细血管受热后会显现出血色,所以毛皮会呈现出淡红或淡粉的样子,这就是‘汗血’之名的由来。这种马体型不算特别高大,但奔跑起来极为迅疾,所以后世很多诗人都在诗中歌颂它。李贺就写了20多首马诗,风格灵动,如‘向前敲瘦骨,犹自带铜声’,把马的神骏写得淋漓尽致。”
在众多写马的诗作中,康震特别强调了杜甫《房兵曹胡马》的独特价值:“这和杜甫的价值观有很大关系。写这首诗时,杜甫才二十八九岁,正是意气风发、蓬勃向上的年纪,诗作也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理想。他把对国家和民族的满腔热情,都倾注到了对这匹马的描写中,所以他笔下的马是‘英雄之马’。你看,‘竹批双耳峻,风入四蹄轻’,‘轻’字用得极妙,既写出了马的速度之快,仿佛在空中飘行一般,又通过‘竹批双耳’的比喻,勾勒出马身体强健、姿态挺拔的模样。耳朵像斜切的竹筒一样耸立,尽显精气神。‘所向无空阔,真堪托死生’,更是直接点出这匹马的品格,主人完全可以将生死托付于它。所以杜甫最后写道:‘骁腾有如此,万里可横行。’有这样的战马、这样的英雄,便能一往无前,这正是盛唐气质的写照。”
李白写下“五花马,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”的千古名句,将骏马与美酒、豪情并列,尽显浪漫主义情怀;韩愈《杂说·马说》以马为喻,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不识人才、摧残人才的社会现实,让马的意象承载了更为厚重的社会批判意义。
这些笔墨中的马,早已超越动物本身,升华为一种精神图腾,其象征的自由、忠诚、勇武、坚韧等品格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。
边疆笔墨里的马与人心
边疆的风雪与荒原,孕育出独树一帜的马之书写。卢一萍以自身边疆经历为底色,将马与高原、边防、生命本真紧紧相连,让笔下之马成为土地与人性的真切映照。采访中,他娓娓道来与马的不解之缘,揭开笔下马意象的精神内核。
谈及写马的灵感,卢一萍直言,边疆军旅生涯是无可替代的创作根基:“我到新疆当兵后才常见到真正的马,军校毕业后去帕米尔高原某边防团当排长,巡逻、执勤乃至日常生活都离不开马,也算一名骑兵。”
这段与马相伴的岁月,催生出《名叫月光的骏马》《七年前那场赛马》等多篇以马为核心的作品,长篇小说《白山》中,马更是关键精神意象。“至少在这些作品里,马是我最核心的灵感支撑。”
在卢一萍眼中,马从不是简单的写作物象,而是具有多重意义的精神存在:“它是我军旅生涯的战友、兄弟,是边疆岁月的伙伴,是我一段文学世界里的精神坐标,也是人性最本真的映照。”
他始终坚信“写马是为了写人”,马与人性最深的联结,在于它是人对话土地、命运的媒介,是照见人心的镜子:“它的沉默照见人的浮躁,它的坚韧照见人的脆弱,它的忠诚照见人的疏离,它的自由照见人的桎梏。马不言语,却用一生的姿态,把人最本真的灵魂摊开在人面前。”
在传统文学中,马多是奔腾的英雄、力量的象征,而卢一萍笔下的马,却带着边疆独有的凛冽与温柔,有着沉默的坚韧、孤独的高贵、悲悯的坚守。
“它们很少肆意奔腾,更多的是在风雪中站立,在戈壁上独行,在绝境中不放弃。”这份独特的塑造,源于他在高原的亲身观察:“边疆的生命从不需要张扬,真正的力量,是在酷寒、风沙、孤独的裹挟里,依然守住内心的温热与坚定。马如此,边疆的人亦如是。我写马,其实也是写这片土地上生命的生存姿态。”
马的坚韧、忠诚与隐忍,让他读懂生命在严酷环境里的尊严,也成为其写马文字的核心:“我写的不是马的形态,而是它在荒原、旷野与人共生的精神底色。”
马年创作,卢一萍依旧与马相伴,这份缘分早已融入笔墨:“并非有意为之。我马年的创作,都会与马有关。”他耗时两年的长篇小说《高原传》即将完稿,另一部非虚构作品中,马也占据重要位置。这些文字,皆是他与马、与边疆的深情联结。
谈及笔下之马想传递给当代读者的精神,卢一萍坦言,是马奔驰不息的生命状态,是兀立荒原、却能在孤独中自洽的品质。若用作品中的一匹马形容马年,他毫不犹豫选择《名叫月光的骏马》里的“月光”:“它骏逸、漂亮,却不像烈马那般张扬,有温柔的底色、明亮的气息,带着诗意与从容,不躁进、不喧哗,却能让人感受到爱。”
在他看来,马年不必一味飞奔、快马加鞭,更应如“月光”一般,清澈、坚定、从容,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光亮。
圣贤先哲以马言志,铸就千年文化符号;当代作家以马喻人,照见世间百态与精神困境;扎根土地的写作者,以亲身经历为墨,让马成为人与土地、与自我对话的桥梁。这些笔墨里的马,不仅是文学经典形象,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脉络,藏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坚守与向往。
文字里的人性思辨
莫言笔下的马,兼具野性与灵性,更承载着对人性、自由与命运的深刻叩问。
在《马语》中,他塑造了一个退役的盲马形象。这匹马曾是战功赫赫的军马,却因不愿让散发着脂粉气息的女人骑乘而被主人鞭打,从此“决定再也不睁开眼睛”。这匹装瞎的马,看似是对主人的反抗,实则是对人性虚伪与强权的无声控诉。马的沉默与坚守,与人类的功利与自私形成鲜明对比,让读者在感叹马的灵性之余,更对人性的复杂有着深刻反思。
谈及马的品性对人生的启示,莫言曾分享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感悟:“马不与牛争快慢,日不与月争明暗,夫不与妻争输赢,兄不与弟争脸面,姐不与妹争温暖,爷不与孙争清闲,朋不与友争人缘,师不与徒争活干。”
在他看来,马的智慧在于顺应本性、不逞匹夫之勇。这种“不争”并非懦弱,而是一种通透的生存哲学。正如他笔下的马,即便被人类束缚、摧残,也始终坚守着尊严与底线,这种品格正是当下许多人所缺失的。
在《狗、鸟、马》中,莫言将德国的马与故乡的马对比:德国的马“太干净、太光滑,没有一点马的野气”,沦为玩物,失却本性;而家乡的马“能跑能跳,狂呼乱叫,很不含蓄”,自由奔放,满是原始生命力。这般对比,既展现了不同文化下马的生存状态,更寄托了他对自由与本真的向往。
“马曾经是人类多么重要的帮手,但现在一点也不重要了。”在这句感叹中,既有对马的辉煌时代逝去的惋惜,也暗含着对现代社会中人性异化的忧虑。
“对藏族人来说,马是有着酒一样效力的动物。”阿来提起与马的渊源,满是感慨,“我很多年没跨上马背,可一看见它们的身影出现在金色桦树掩映的路上,身上所有关于这种善驰动物的感觉便瞬间复活!那种强健生命特有的腥膻味,蹄声在寂静中震荡,脊背波浪般的起伏,和大地一起扑面而来的风,这就是马。”
但他笔下的马,却带着复杂的矛盾感。“我见过的那些山地马,矮小、毛色驳杂、了无生气,主人都叫它们牲口。”阿来回忆故乡见闻,“它们松了缰绳也不去寻自由与水草,反而把长脸伸到你面前,呼呼喷着热气,只为讨要一点机器制造的食物。我的那一匹,甚至会从我手上舔走方便面和夹肉面包。”
可在月光下,这些“牲口”会展露截然不同的模样。“半夜醒来,月光洒在地上,那些马一匹匹立在清辉里,卸去简陋鞍具,月光掩去所有挑剔细节,只剩粗粝轮廓。”阿来描述那个寒夜,“那一刻,它们重新成了布封笔下赞誉的马——豪迈而狂野。行走轻捷,轻轻一跃便能登上雪水冲蚀的堤岸,林中一丝细微响动,耳朵与尾巴便陡然竖立。”
这种反差让阿来陷入深思:“它们的祖先也是从草原上来的,是沦落了的一群。为了适应山地,它们高大的身躯日渐矮小,来对付复杂的坎坷,这原本无可厚非。可它们同时传递了认命的悲哀,逆来顺受,荡尽了英雄气息,才沦落为‘牲口’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继续说道,“我忽然意识到,人在社会里,从遗传、从四周环境不断得到的沦入平凡、甘于平凡的指令,不断丧失个性的过程,早就在生物界演示过了。”
贾平凹在作品中多次以马为喻,笔下之马常与黄土地相连,是坚韧、朴实的乡土精神象征;张贤亮在《灵与肉》中,借主人公与马的相处,展现人性的复苏与精神的觉醒。
这些文字里的马,意象愈发丰富多元。它们不再是单纯的精神图腾,而是承载社会现实、人性困境与精神追求的复杂载体,为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
-

数字版
-
11 天府周末